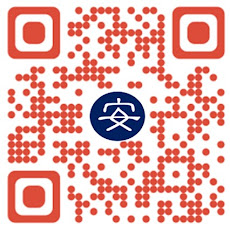【新南向論壇】陳麗郁:南向詮釋──人、文化與博物館
2016/05/26
劉抗:水上人家,收藏於新加坡國家美術館。
「We asked for workers. We got people instead.」(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瑞士作家Marx Frisch的興歎,早已遍佈每個僱用外籍移工的國家之中,包含臺灣。一直以來,臺灣對東南亞的認知,始終停滯在這樣文化不對等的狹隘思維之中,對人文(Humanity)層次的思考近乎失能,眾人卻視若無睹。
有幸與會「新南向政策論壇」,我們得以知悉「新南向政策」積極擘畫與東南亞連結的遠大藍圖,打著「多元」及「以人為本」口號,實際推動的其實是「加碼投資」、「把東協視為臺灣的內需市場延伸」的政策方向,然後說要以熟悉東南亞人才培育為輔。若我們不過分嚴苛地把這些想像與日本殖民統治下,為了侵略東南亞與穩固殖民帝國所推動的「南進政策」、「內地延長主義」聯想在一起;若寬容檢視,實在也很難將這樣的口號與「以商業利潤為本、政治策略為輔」的眼前利益脫鉤。我們不禁要問:新南向政策的「人」是什麼?「人」又在哪裡?
▋不只看到人力,更看到人文
若新南向政策的「人」只停留在「Human Resource」層次,在缺乏文化視野與對話的對等基礎上,所謂「人才培育」背後,仍然直指市場大餅的卡位戰鬥人力。短淺且粗糙的政策制定,無疑只是另一次對彼方土地、自然、人力等資源的瓜分與搶奪,甚至淪為臺灣自我膨脹的一廂情願,罔論能引起南方的共鳴或迴響。
人類學家郭佩宜曾經撰文〈如果總統是人類學家〉,她充滿創意地以人類學觀點切入公共事務,強調人類學家面對「差異」(alterity)的敏感、好奇與謙卑,具備全貌觀(holism)思考等特質,作為對政治領導者或工作者具備能力的想像。郭佩宜老師的幽默並不是要我們找一位人類學家來任事,她提醒我們,現今的政治工作者是否能具備寬廣的文化思考,以差異理解、對話與溝通的互動模式,制定與執行更具「人文」觀點的穩健政策?
如果我們將新南向政策的「人」定義為「Humanity」,不但打破國家政治的疆界、經濟利益的短近侷限,更能站在「跨文化」的全貌角度,思考如何與東南亞進行多元互動。人類學家告訴我們理解尊重文化差異的重要性,從穆斯林到錫克教徒、從魚露到參峇醬、從山林遊牧到湖上人家、從亞齊的漁村到仰光的佛塔,這些對於臺灣人都陌生至極的文化實踐,卻是東南亞某處的日常經驗。這樣遙遠且陌生的文化距離,在時空限制與缺乏認知基礎下的臺灣,我們又該如何拉近與東南亞的距離呢?
有人說從善待東南亞移工開始,有人認為從學校教育著手才是關鍵,有人認為所謂「新二代」是重要的橋樑、有人也說其實應該提升臺灣人的國際觀,更有人覺得,應該直接到東南亞去交朋友、把他們當「自己人」就沒問題;眾聲喧嘩之中,政府身為推動新南向政策者,能為拉近與東南亞距離做些什麼呢?我認為,「博物館」絕對是歷久彌新的能量聚合體之一,也是國家最能驅動的文化能量之一。
▋從博物館出發的文化可能
新世紀的博物館已經從寶物秘庫般「被動」的角色,拓展到刺激社會文化對話的「主動」催化劑,博物館可以與個人、家庭、社區、族群、國家、世界產生對話,更可以蒐藏展演從文化到知識的物質物件與抽象概念;其所能運轉的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等多元能量,已遠超越我們所能想像。新加坡,作為一個東南亞的重要金融商業與轉運中心,對於東南亞、乃至於全亞洲、全世界的主體想像與實踐,均表現在其對博物館建構版圖之上,從新加坡政府經營博物館的視野,我們可見其勇於實踐作為東南亞文化藝術對外埠口,並具備與世界溝通的領航地位。
新加坡有兩座與亞洲藝術文化相關的國家博物館,一座為1997年就佇立新加坡河畔的亞洲文明博物館(Asian Civilisation Museum),另一座則是2015年甫開幕,融合新加坡高等法院與市政廳兩大重要歷史建築的新加坡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前者專注在亞洲地區物質文化的蒐集與研究,是今日亞洲地區跨越西亞、東亞、南亞與東南亞典藏研究質量兼備的先驅博物館機構;後者則是挾著「世界第一」的東南亞現代藝術蒐藏地位,並以氣勢滂礡的國家歷史建築作為後盾的嶄新東南亞美術館。
現代藝術的詮釋,有著新加坡美術館(Singapore Art Museum)、新加坡雙年展(Singapore Biennale)與新加坡藝術節(Singapore Art Festival)等固有藝術社群作為本地動態後盾;歷史文化的亞洲觀點,則透過新加坡本地十數間博物館及歷史中心,展開新加坡與東南亞、新加坡與亞洲,甚至新加坡與世界的對話漣漪。我們看到一個城市國家對於文化戰略的定位明確與行動清晰,透過博物館的展演、典藏研究、教育活動等主動能量運作,國家足以展現其對文化的發語權。透過博物館所傳達出一個訊息:無論是時間縱深抑或空間橫剖,新加坡不再只是新加坡,她是東南亞的新加坡、亞洲的新加坡,也是世界的新加坡。
我們從新加坡博物館版圖擘畫中,看見他們如何將文化藝術、歷史社會詮釋及展演定位為自身與東南亞關係的強大辯證。然而,我們不可忽略,在博物館中,「人」是觀看、思考與實踐的主體,也是連結社會文化、生活經驗的客體,「人」與「文化」在博物館不斷交互生產論述、創造當代的觀點。我們反求諸己,臺灣對於東南亞人文藝術的耕耘田野在哪裡?國家與民間投注多年的博物館能量,是否能充分觸及與東南亞文化對話的深度與廣度?以博物館作為「人」與「文化」載體,我們與東南亞的多元交流與溝通,是否能跨越藩籬與侷限,活用既有資源,創造更多文化對話的可能性?「南向」的文化詮釋,若能透過國家整合臺灣博物館界集體知識與藝術能量,作為接點向外延伸,開啟與東南亞藝術人文之人才、社群、機構等長期穩定之合作交流,我們或許可以期待兩地文化社會擁有溝通平台,透過彼此理解作為南向瞭望與對話的基礎,更可作為臺灣立足世界的新視野。
(作者為暨南大學東南亞所研究生,本「新南向論壇」系列文章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與獨立評論合作刊登)